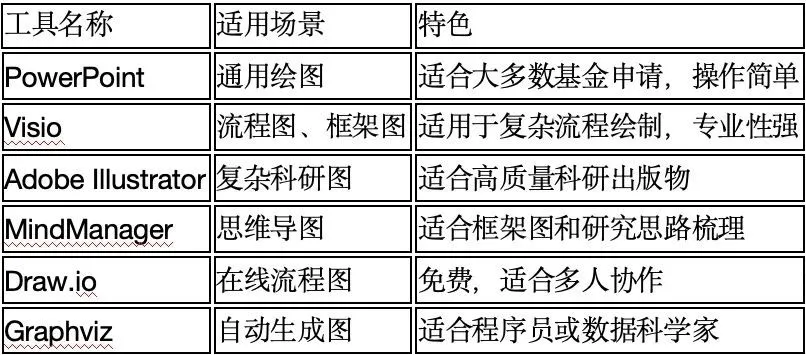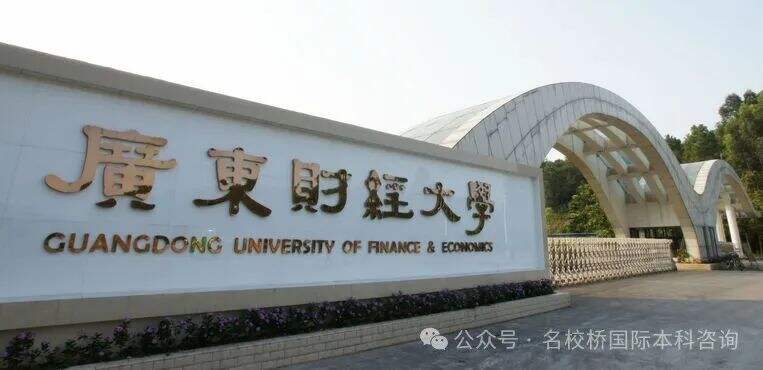重点学术期刊的选题风向,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切片。
翻开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24年总目录,就像打开了一面棱镜——既有对国家战略的精准呼应,也有对文明基因的深度解码;既能看到数字浪潮对传统学科的冲刷,也能触摸到知识生产场域中“中国性”的自觉建构。
这些选题背后,藏着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底层密码,值得我们去深深探讨与把握。
解题式研究:把“国家命题”转化为“学术问题”
这一年最醒目的特征,是学者们集体展现出一种“解题自觉”:不再满足于对政策文件的注解,而是用学术话语重构国家战略的深层逻辑。
比如“中国式现代化”这个宏大主题,不同学科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题路径——
马克思主义学者丰子义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提炼出“总体性方法”,把现代化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比作“双向校准的陀螺仪”。经济学者曹廷求团队则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数据作“探针”,解剖结构性货币政策如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“血管支架”。
这种跨学科解题的背后,是对“现代化”概念的解域化:它不仅是经济指标,更是文明形态的迭代。
更精妙的解题出现在细微处。当“新质生产力”成为热词,黄群慧没有停留在概念阐释,而是将其置于新型工业化的历史坐标系,揭示出生产力跃迁对全球产业链“拓扑结构”的重塑效应。
这种把政策话语转化为学术问题的能力,就像把阳光分解成七色光谱——既保留了原初能量,又呈现出更丰富的认知维度。
知识考古:在传统褶皱里寻找未来密码
去年历史学板块堪称“文明的CT扫描”。从李雪山对商代礼乐制度的解码,到万明重勘明代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坐标,学者们正在进行一场“反向解构”——不是用现代框架切割传统,而是让古老文明成为诊断当代的“试剂”。
最典型的案例是王祁对商周“五域天下观”的阐释。当他把“中域”概念与当代地缘政治结合时,传统天下观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青铜器,而变成了理解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认知工具。
这种研究路径,暗合了孙周兴在现象学存在论中提出的“寂声与黑白”——在无声处听见文明的呼吸,在无色处看见历史的色谱。
文学研究同样在“传统的现代性”中开掘。汪涌豪团队对古文论形式批评的再发现,像极了文物修复师的工作——用“声”“色”“体裁”“句调”等传统范畴,拼凑出中国文论独特的认知基因。
当这些基因与孙玮提出的“破域”媒介论相遇时,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突然有了历史纵深感。
范式革命:当数字逻辑撞上人文地基
去年最激烈的思想交锋发生在数字前沿。法学界马长山提出“三维世界”的数字法学框架,把数据权利比作“液态金属”——既要有容器的刚性,又要保持流动的活性。
这种比喻背后,是传统法学范式在算法权力面前的集体焦虑。而廖备水关于机器伦理的论述,则试图在“弱主体性”与“社会平衡性”之间走钢丝,这种理论冒险堪比在数字深渊上架桥。
更具颠覆性的是方法论创新。何丹团队从汉语口误现象切入,竟推导出人类语言认知的“光子模式”,这种跨学科脑洞让人想起爱因斯坦的思维实验。
而李芳华用企业区位选择数据构建的“决策树模型”,把经济学变成了“社会物理学”,在数字与现实的纠缠中寻找规律。
但最意味深长的转变发生在底层逻辑。当陈波试图用“需求—目标—原理”链条弥合“是”与“应该”的鸿沟时,他实际上在数字时代的确定性迷思与传统人文的模糊性智慧之间,搭建了一座临时浮桥。
这座桥能走多远,或许决定着人文学科在算法时代的命运。
知识生产的中国性:从“接着说”到“重新说”
这一年最值得玩味的变化,是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”从口号变成了方法论。郭忠华提出的标识性概念建构“四原则”,像极了知识工程师的蓝图——既要保持概念的“语义纯度”,又要预留“谓述接口”。
这种精密设计,折射出中国学界从“学徒心态”到“主体自觉”的集体转身。
在具体领域,这种转身更加生动。当邹元江批判戏曲美学中的“概念置换”时,他实际上在捍卫中国艺术的解释主权;李怡对“文史分合”的再思考,则试图在学科建制中找到中国文论的元代码。就连王思豪重释“赋史”传统,都暗含着与西方“史诗”话语分庭抗礼的野心。
这种知识自觉甚至渗透到技术哲学领域。肖峰用历史唯物主义解剖大模型,提出“智能社会”不是技术奇点而是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。
这种论述方式,既跳出了技术决定论的窠臼,又避免了庸俗唯物论的陷阱,展现出中国学者特有的辩证智慧。
未完成的叙事:在断裂处生长
在这些光鲜的学术景观背后,仍有一些裂隙值得警惕。比如对数字劳工、算法歧视等前沿议题的关注不足,暴露出学术回应现实的速度滞后;再如乡村研究多集中在经济维度,对数字乡村的文化嬗变缺乏深描。
吴忠民关于农村变革奠基性影响的论述,更像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,而非对未来挑战的预判。
更大的隐忧藏在知识生产的结构性矛盾中。当“中国性”成为学术政治正确时,如何避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?当量化方法席卷人文领域时,怎样守护“不可量化的价值”?
徐向东对道德生物增强的审慎,李景林对“本义价值”的坚守,提示着我们:在知识创新的狂飙中,仍需留一片沉思的净土。
在解谜与造谜之间
2024年的《中国社会科学》,像一座正在施工的学术立交桥——既有夯实路基的传统研究,也有伸向未知的理论高架。
这些选题共同勾勒出一幅“新知识地形图”:X轴是“中国问题”的纵深感,Y轴是“文明对话”的开阔度,Z轴是“数字转型”的穿透力。
当我们穿行其间,既能触摸到历史深处的文化基因,也能听见未来文明的先声。
或许正如刘梁剑所言,“古今中西”之争已演化为“交相发用”的结构。在这个结构里,每个学者都是摆渡人——既要解开时代的谜题,也要为后人留下新的谜面。而真正的学术生命力,恰恰藏在这种解谜与造谜的永恒辩证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