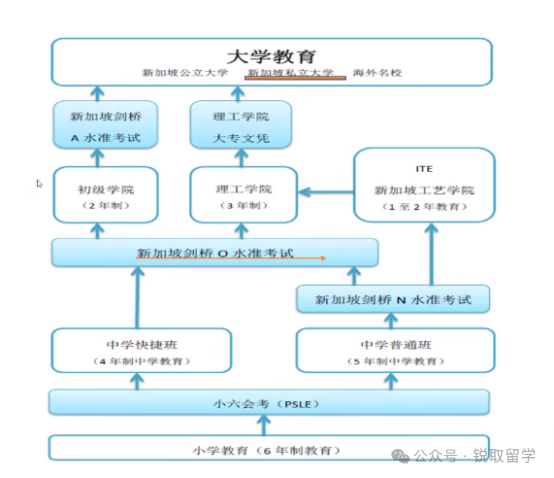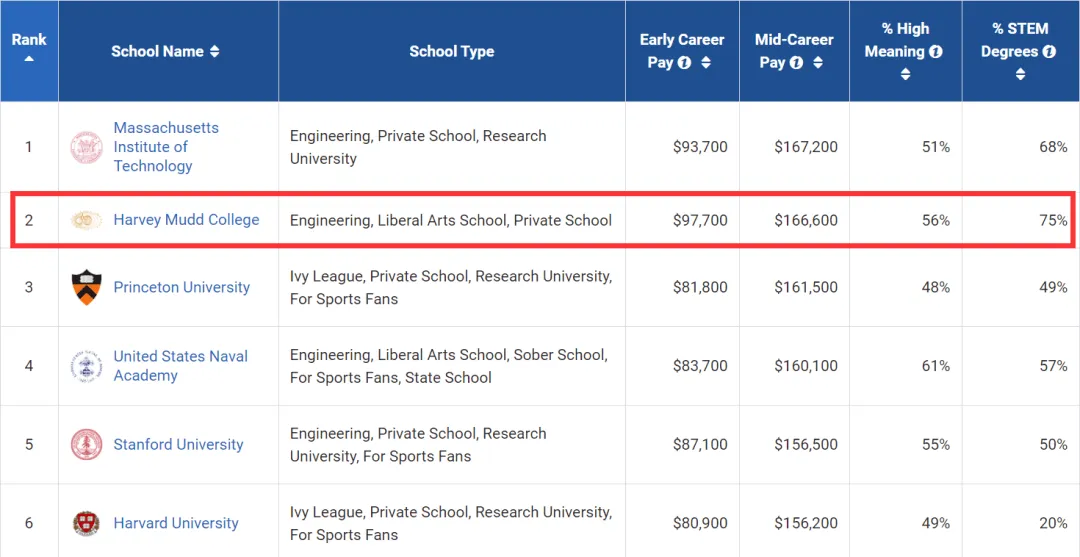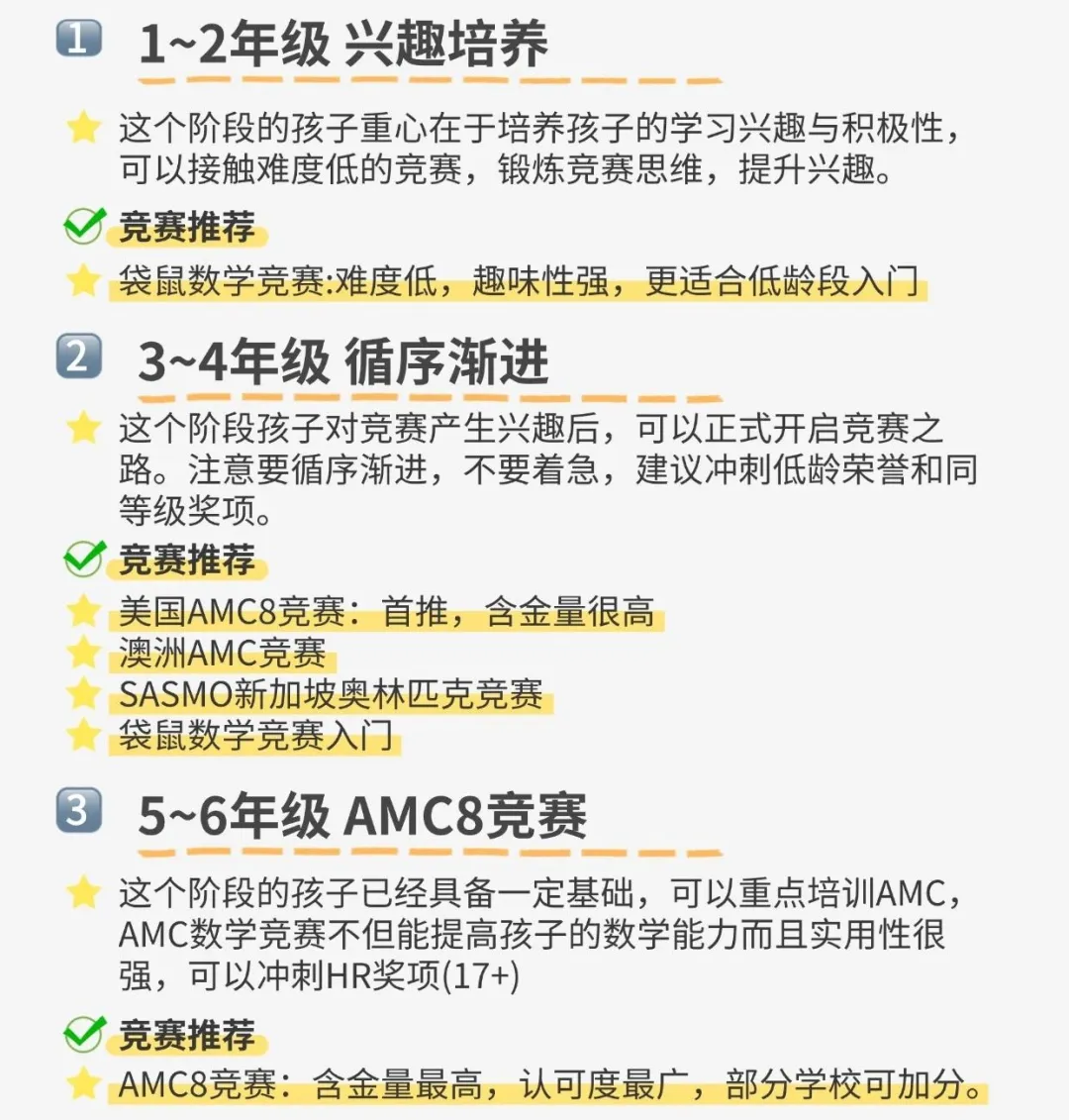什么是大学?为什么面对面教学在数字时代仍有价值?
原文选自《TLS》以下为中文版本由Bruin留学工作坊翻译:
作者:Joe Moran ,乔-莫兰是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英语和文化史教授。他的最新著作是《如果你失败了》:安慰之书,2020 年
在平时,秋天对我来说意味着新的开始。空气中弥漫着第一缕潮湿的寒意,树叶凋零,就在我们的鸟类夏日客人纷纷南下的时候,学生们一波一波地赶来了,他们相互拥抱,像从非洲归来的燕子一样尖叫着。
这个自我补充的部落大多年轻,四肢松弛,善于表达,让我不禁感叹岁月的流逝。我电脑里的文件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老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觉得他们的渴望很吸引人。大学新学期的第一天就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:黑板擦得干干净净。这种季节性迁徙也可能是致命的。成千上万的新生乘坐父母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来来回回,然后聚集在一起,交换细菌。
时间安排软件以微小的同步小型迁移方式将他们带到各个教学楼,每小时形成走廊瓶颈。走进一间刚搬空的教室,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汗臭和香水味。这里是吸血鬼病毒的温馨栖息地,它们通过在其他活体上蹿来蹿去而茁壮成长。大多数大学讲师都经历过新生流感的多次反复。暑假期间,我逐渐意识到:到了九月,一切都将变得不同。大学将提供 "混合式学习"--更多的在线教学,更少的接触时间。
与此同时,有关大学的新闻也令人沮丧。支付较高国际学费的中国和印度学生的巨大市场一夜之间崩溃了。财政研究所警告说,13 所英国大学或学院面临破产风险。一些大学要求员工减薪。还有一些大学宣布关闭人文学科学位。许多签订短期合同的讲师在学年结束前被解雇,而这些讲师在大学教学中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。7 月,加文-威廉姆森(Gavin Williamson)领导的教育部公布了一项 "重组制度",概述了大学申请紧急贷款的条件。
这等同于一项新的高等教育政策,包括急剧转向 STEM 和职业课程,威胁停止资助被认为性价比不高的艺术和人文学科课程,并警告说大学将无法避免破产。即使在困难时期,大学也很少得到同情。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,大学始终受到低层次的敌视。正如威廉-怀特(William Whyte)在《红砖:英国公民大学的社会与建筑史》(2015)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,我们往往不是把大学作为一个地方,而是作为一种理想来关注。他认为,这导致 "人们不断感到大学处于危机之中,无法实现这一崇高、固定和虚构的理念"。
近年来,大学被斥责为藏污纳垢、反市场思想、自以为是的留欧主义和觉醒政治的避风港--用托比-扬的话说,就是 "左翼宗教学校"。但大学并不是这些狂热想象中的任何一种东西。首先,它是一栋建筑,或者说是一组建筑,由砖块、玻璃、地毯和塞满管道和电缆的天花板组成。这里不仅有学生和讲师,还有办公室工作人员、清洁工、辅导员、餐饮服务员、图书管理员和会计。
在教室里,你会发现人们在谈论合同法或李尔王,或在福音唱诗班唱歌,或排练戏剧,或跪在祈祷垫上,或躺在瑜伽垫上。这些人和这些建筑在千千万万个细小的行为中汇聚在一起,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、不断发展的集体有机体。一所大学就像一个小镇一样,充满了人类的美德、怪癖和缺陷,而且难以概括。
在《建筑如何学习》(How Buildings Learn:在《建筑是如何学习的:建筑建成后发生了什么》(1995 年)一书中,斯图尔特-布兰德对麻省理工学院一座占地广阔、破旧不堪的建筑大加赞赏,这座建筑被称为 20 号楼。20 号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雷达研究而建造的临时建筑。到 1998 年最终拆除时,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已经容纳了有关语言学、声学、微波、电子游戏和高速摄影的开创性研究。
它采用横向布局,有许多走廊和一台大家都趋之若鹜的自动售货机,迫使人们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。这是一个租金低廉的环境,没有地盘之争,因为这里的地盘--漏雨、通风、破旧--不值得争夺。核物理学家杰罗尔德-扎卡里亚斯(Jerrold Zacharias)正在研究第一台原子钟,他只需在地板上凿洞,就能为他的设备腾出空间。20 号楼的存在让创造性的事情发生了。
如果大学不是一栋建筑,那它又是什么呢?我们现在有了一些概念,因为在今年 3 月,大学不再是摆放着翻转式讲台座椅、聚丙烯课桌椅、隔音板和有关消防集合点的层压告示的物理空间。它们变成了数据包,通过光纤电缆和无线路由器传送到厨房餐桌、后卧室和花园棚屋。讲座在网上录制,网络研讨会在网上举行,论文在网上提交和批改。这或多或少起了些作用--但就我个人而言,这是一项枯燥而孤独的事业。
我尤其为我们的毕业班学生感到惋惜,他们只需点击一下鼠标,提交最后一份作业,然后在备注栏里给导师留下简短的备注("我知道这份文件被称为'即将完成',但我向你保证,它确实已经完成了",我的一个学生如是说),就结束了他们的大学生涯。就这样,他们的学生时代结束了。在科维德-19 就业市场的寒风中,他们没有告别拥抱和学位授予仪式等温暖的仪式,而是被遣散了。网络大学之所以成为可能,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,教学逐渐实现了数字化。
第一步是 PowerPoint,英国大学很晚才采用。我的硬盘告诉我,我是在 2003 年才开始使用它的,也就是在那一年,耶鲁大学教授爱德华-塔夫特(Edward Tufte)抱怨说,PowerPoint 演示文稿 "太像学校的戏剧了:非常吵闹、非常缓慢、非常简单"。
但是,PowerPoint 有一个很大的卖点:它的要点模板和即插即用的设计可以很容易地插入内容。在更加市场化的大学系统中,它可以消除讲师的个人特异性,并满足演示能力的基本标准。讲课幻灯片还可以添加到 VLE("虚拟学习环境":充满教学资源的电子门户网站)中。
最近,这些资源不仅包括幻灯片,还包括讲座录音。虚拟学习环境响应了与电视追看和流媒体服务相同的需求:个人消费者希望在方便的时候以异步方式获取内容。
新技术与面对面教学一起使用,效果很好。长达一小时的实时讲座这一神圣形式可能需要颠覆。这种教学方法是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发明的,当时书籍和纸张匮乏,课文必须通过朗读才能讨论。齐格弗里德-沙逊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剑桥大学学习法律的短暂时光,他尽职尽责地参加 "喋喋不休的讲座","记笔记似乎是一种体力而非脑力锻炼"。
在《胜利的牛津》(Oxford Triumphant,1954 年)一书中,应届毕业生诺曼-朗梅特(Norman Longmate)认为,讲座这一中世纪的发明 "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,成为牛津最浪费时间的东西"。在一次演讲中,朗梅特注意到一位同学正在创作十四行诗,另一位同学正在为身边的女人画素描。大学的黄金时代从未出现过。我曾是一名学生,那是全额生活补助和政府对高等教育轻微干预的垂死年代。那个世界有太多漫不经心、自满沉闷的讲师,他们认为教我们是一种强加。
对学生的消费主义来一剂猛药,似乎再合适不过了。除了一个顽固不化的细节:学生不是消费者。他们不是为学位买单(如果是这样,他们的学位证书就一文不值了),而是为学费买单。学生要接受评估、打分和等级评定,这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是不可能的。教学不是面向客户的服务,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等级活动。同时,它也是社区性和协作性的。随着追看和流媒体服务改变了我们观看电视的习惯,失去的只是散落在数百万客厅中的散居式现场观看社区。
但是,当学生们在闲暇时阅读课堂材料时,课堂的agora就变得贫乏了。在学生满意度调查中,原本共同的追求变成了个人喜好的统计汇总。每个讲师都知道这样的规律:学生进入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手机插入教室的插座。就像贝都因人在井与井之间仔细校准羊皮包里的水能流多远一样,他们总是在往返充电点的路上。我认为课堂教学是对他们设备驱动型生活的一种矫正。课表上的课堂不可避免地是模拟的。它不能以双倍的速度观看(这是学生对录制的讲座的一种惯用伎俩),也不能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内容。
它教会他们真正地置身于一个房间里,知道当思想和言语从这个集中的共同关注的气泡中流出时,它们才具有真正的分量。所有的人类交流都是体现性的。开了一天的 Zoom 会议后,你的头痛也说明了这一点。即使思考也会消耗卡路里。
我们是感性和触觉动物。这就是为什么录制的音乐没有扼杀音乐会,为什么球迷们聚集在城市广场上通过大屏幕观看足球比赛,而他们在家里也能轻松观看,为什么朋友们更愿意亲自见面而不是通过 FaceTime。我们最热衷于接触的不是头像或会说话的矩形脑袋,而是其他会呼吸的躯体。教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教学不是商业交易,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行为。与大多数动物不同,我们是早产儿,大脑和神经系统仍在发育。即使是简单的运动功能,我们也需要多年才能掌握。因此,我们依赖长辈教我们做什么和如何生活。这让我们变成了需要帮助、喜欢模仿的动物,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而受到伤害,或者因为别人最轻微的点头赞许而变得高高在上。
教学依赖于手势、肢体语言、眼神交流和声调--这些几乎不易察觉的东西让每一次谈话都与众不同。一堂好的大学课取决于伊丽莎白时代所谓的 "生动的转折"--在瞬间产生的令人惊讶的联系、点缀和思想飞跃。在录制讲座时对着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说话,这与现场戏剧的台词朗读是不一样的。大学的规划者们已经开始讨论 "粘性校园":一个拥有大量社交空间的校园,这样学生们就能在课前和课后留下来。
说到重新发明轮子。在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的记忆中,黏糊糊的校园就是 "校园"。约克大学、苏塞克斯大学和兰卡斯特大学等 20 世纪 60 年代开办的多科性大学的校园都非常拥挤,部分原因是意外。它们需要至少200英亩的土地,而市中心的地价太高。因此,这些学校都建在城外的绿地上。红砖大学生通常住在家里或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宿舍里。
但当我的父母于 1964 年作为兰卡斯特大学第一批学生的一员来到兰卡斯特大学时,他们遇到了中世纪大学理想的复兴,即大学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者社会。如今的学生,很多都住在家里,并通过有偿工作来补贴学费,他们没有这种奢侈的生活。但由于他们的生活更加支离破碎,大学为他们提供归属感和社区感就显得更加重要。在线教学通常被认为是为学生提供灵活性和可及性的一种方式,只需点击鼠标,一切尽在掌握。但这也让他们回到了自己分配不均的资源上。
停课暴露出的一个问题是,有多少学生在家里没有电脑或安静的工作场所。任何教过年轻人的人都会发现焦虑和抑郁流行的症状。焦虑学生的一个共同特点是,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头脑中--一个呼呼作响的有线头脑,已经与他们拖着的躯壳疏远了。作息时间和时间表可以帮助他们:保证充足的睡眠,定时定量进食,在课间、走廊闲聊和喝咖啡的间隙加入临时组成的学生团体。学生们可能会对手机爱不释手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或想要在网上过一辈子。
大学的管理者往往是技术乐观主义者,对数字化这个词有一种神奇的魔力。相比之下,大学的作息时间则会让人感觉枯燥乏味。然而,每周在同一时间出现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。它能让你克服乏味、疲劳和失去信心的感觉,而这些感觉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。真正的学习需要耐心、循序渐进的努力,而习惯则是支撑这种努力的脚手架。
时间表也是我们对他人忠诚和承诺的挂钩。2001 年,玛格丽特-德拉布尔在牛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:小说家安格斯-威尔逊是东英吉利大学的英语教授。他退休已久,身体不好,住在法国南部,有时晚上会突然从床上爬起来,匆匆忙忙地拿起一堆文件,说自己要 "去做讲座"。他的搭档托尼-加勒特(Tony Garrett)最终会说服他不要去演讲,并劝他继续睡觉。我担心这可能很快就会变成我。
我还能再在座无虚席的教室里讲课吗?我担心大流行病会加速一种潜在的趋势:大学被重塑为一个虚拟的、原子化的、空洞的空间。政府的重组机制指出,适应后科维德世界可能意味着 "最大限度地发挥危机所揭示的数字化和在线学习的潜力,以提高可及性"。
在线教学需要的人员更少,可以削减管理费用,并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--至少在成本低廉的情况下是这样。由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而必须建立的数字化大学,可能看起来是对其劳动密集型前身的一种改进。但失去的是大学教育中那些无法量化的方面,这些方面无法简化为可打包、可下载的内容。
学生不仅仅是人力资本,而且是有创造力的、骂人的、非算法的、不可复制的独特的人。他们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发展自己的特殊天赋,让自己感到真实并对他人有用。古希腊人将这一教育理想称为 eudaimonia,即 "人类繁荣"。作为大学的理由,它是一条倒退了几条战壕的防线,难以审计或计算,而且很容易被讽刺为胡思乱想。
但是,大多数大学教师仍然以某种抽象的形式认同这一观点。他们认为,如果不认识到大学作为一系列有机的、偶然的邂逅所具有的价值,狭隘地追求市场效率很可能会被证明是毫无乐趣和自取灭亡的。他们认为大学是一个地方,他们希望当这一切结束时,大学将再次成为一个地方。